庆贺薄松年教授从教60周年座谈会
2016年5月6日,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薄松年先生从教60周年座谈会在故宫西华门外泽园举行。故宫研究院副院长兼研究室主任余辉先生主持了会议。——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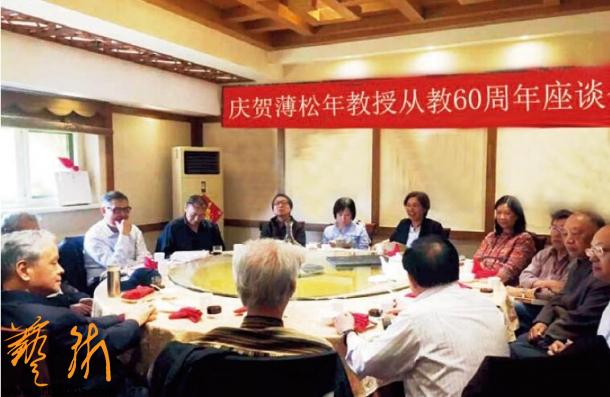
庆贺薄松年教授从教60周年座谈会现场
余辉(故宫研究院副院长兼研究室主任):
这次来参加庆贺薄松年教授从教60周年座谈会的主要是故宫出版社出版的《宋元绘画研究》的部分在京作者和《艺术》杂志执行总编杨庚新先生。薄先生是故宫研究院古书画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为故宫博物院培养了许多书画业务人员和爱好者,因此这次是以故宫研究院的名义来举办出版座谈会。在座有很多薄先生的同道和弟子,希望大家开怀叙说,回忆薄先生的教学感受,或者结合目前宋元绘画研究的热潮进行讨论。外面有一个展示台,摆满了薄先生的著作,大家可以去欣赏翻阅,里面有很多是我们当年用过的教科书。

薄松年教授
薄松年:我虽然年纪比较大,但组织这样的活动是很少的,心情非常惶恐。我给自己一个定位,既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我只是教书匠。这个教书匠还不是艺术教育家,艺术教育家是有成就的,我没有成就,只能算是教书匠。但是我一辈子对教书行业是很有热情的,责任感是很强的,总是在踏踏实实地教。在我写的东西里,教材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我常常说,我写的和教的是“百三千”,就是《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是小孩刚开始学习的基础,虽然是基础,但是非常重要。现在一些学术论文或者研究专题,选题很好,切入点也很好,但有时就在基础上出了硬伤,这就影响到整体的水平。大家一起做《宋元绘画研究》这本书算是一次笔会了,希望通过这本书我们能够在宋元绘画上做一些交流,这既是一个学术活动,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和鼓励。
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听过薄先生的课。工作时,薄先生又支持我工作,当了一年多的副系主任。我讲这么几点:第一点就是薄先生博闻强记,记得薄先生讲课,说到元世祖让赵孟頫写诗讽刺留梦炎,薄先生当场倒背如流,让我印象尤深。去年在杭州开宋画国际研讨会,年轻朋友发言中引文出错,薄先生不用查书,当场纠正。第二点是教学和研究并重,并且更重视教育。前些年乔迅(纽约大学教授)出了一本书,写着献给薄先生,我就想起来我读研究生时,乔迅也在美院听课,下课时经常围着薄先生提问,后来他的书虽然是研究石涛,但他觉得跟薄先生学习受惠最多。再有,薄先生还是一个学者之间进行合作的榜样。薄先生跟陈少丰先生合作,进一步整理、完善王逊先生的美术史讲义,写成了《中国美术史教程》。美术史学者之间的这种合作不是很多,所以这很难得。薄先生还和陈先生合作研究《林泉高致·画记》,在这方面薄先生还受教于启功先生。
薄松年:对郭熙儿子郭思《林泉高致·画记》的研究是启功老师给我提供的材料。他本来自己做了校订交给人民美术出版社,但到现在也没出版。我一直在催问启先生的稿子到哪儿去了?那都是启老亲自写的,很有价值的。
薛永年:薄先生在教学研究里,不仅通,还很专。刚才讲到的宋元研究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年画、民间美术,他是重要的拓荒者之一,过去的研究都是以文人艺术为主,民间美术是空白,薄先生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影响也很大。
薄松年:我很喜欢民间美术,王逊先生让我在这方面多做一些事情,因为这块在美术史上是一个空白。现在我填补了一部分空白,但也没有完全都填补上。
曹星原(加拿UBC大学教授):
我补充一句,九几年的时候薄先生到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把年画研究带到了美国,薄先生和历史系的大卫·杰逊合作,进行美术史和历史的跨界研究。那时候加州大学是社会学美术史研究的重镇,风潮正盛,他们二人的合作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在薄先生离开之后,很多硕士生、博士生的毕业论文选题都是中国民间艺术方向,都受到薄先生的影响。
单国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我在学校的时候听过薄先生讲课,后来一起参加过很多研讨会,薄先生岁数最大,但又总是参加。研讨会每年的题目都不相同,跨度很大,文章很不好做,我有时都疲于应付。而薄先生每次参加都带着论文,给一个题目就能写文章,这让我非常佩服。有一次讲《清明上河图》,薄先生也没有发言稿,上去就讲,谈当时有多少本《清明上河图》,这些《清明上河图》都是怎么回事,还联系了当时苏州地区的社会情况,大家都觉得很有深度。薄先生熟悉通史,又对很多专题有比较深的研究,触类旁通,才能够信手拈来。这样做学问是一条很好的路子,先有通史的基础,然后再来做专题,专题也不能死抠某一个,而是社会上需要哪个专题,你拿来就能够深入下去,把它研究出来。要有这个本事,才能把学术活跃起来,才能出更多的成果。

薄松年教授编著图书
聂崇正(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我上学的时候,薄先生没有教过我,但是我从各个渠道了解到薄先生有三个特别认真的地方,一是备课特别认真,二是讲课特别认真,三是课后辅导特别认真。薄先生做美术史教学时的这种认真态度,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是很少见的。
李福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前面三位都是我的师兄,我是1966届的,薄先生刚好教我们。我印象非常深的一点是,薄先生对学生可以说是无私的,他的教案和讲稿,讲完课以后就放在讲桌上,大家都可以传看,没有任何的保留。薄先生主讲宋元,这对我工作以后的学术侧重点是有直接影响的。我教学以后对宋元特别感兴趣,就是因为当时薄先生的课材料丰富又生动有趣,把美术史和当时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讲得就像说书一样,让人印象深刻。如果说薄先生是教书匠,我就是小教书匠。薄先生的教书匠不是一般的教书匠,是高品位的教书匠,既教你学问,也教你做人。薄先生八十几岁仍然笔耕不辍,成果不断,精力比我们还旺盛。薄先生教了那么多学生,很多学生都念念不忘薄先生的好处,而且有一些学生还在学术界有所贡献,这是对老师最大的安慰。
杨庚新(《艺术》杂志执行总编):
我和福顺学兄是一个班的,薄先生在中国美术史这个领域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当时我们班很多人原来是学历史、学文博的,中国美术史方面是一个比较生疏的领域,是薄先生把我们引到这个门径里面来的,这中间所花费的心血可想而知。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几乎每个晚自习薄先生必到,检查作业、笔记,看有没有漏记的,有哪些弄不明白的问题。不夸张地讲就像慈父一样,希望我们尽快走上学习的正道上来。另外,薄先生还有一种非常执着的精神。80多岁高龄还伏案写作,《艺术》杂志需要稿子,基本上是我们需要哪方面,薄先生就提供哪方面,不止是年画这一块,生肖方面也给我们写了不少好文章。薄先生的研究领域是非常宽的,在美术史普及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借这个机会代表《艺术》杂志感谢薄先生,希望薄先生继续为我们做工作,做宣传,做研究。我们也要学习薄先生这种精神,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
巫鸿(芝加哥大学教授):我是美院63级的学生,“文革”以前的最后一届。我和薄先生接触不多,一是刚入学的时候,听过薄先生的课,薄先生那时的形象在我脑子里还很生动;一是在美国的时候总会听说有学生在中国的时候向薄先生请教了问题。我们学校最近做了一个展览,涉及到民间艺术方面,就有很多问题向薄先生请教。
我刚进学校就赶上大乱,真正上课的时间也就一年多。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时还是学了不少东西的,这主要得益于在那么高压的情况下,还有一些像薄先生一样敬业的老师在讲学术,我对这点印象很深刻。有时我觉得现在的教育体系那么健全,按部就班地教和学,反而不一定能产生很多东西。
薄先生自己也说,他不是传统的文人式的知识分子,他的研究方向从宋元跨届到民间艺术,现在看是一种比较新式的研究方式。薄先生开始得很早,现在还在持续,现在可能还看不太明白,将来回头一看就清楚了。就拿美院来说,美术史系成立有半个世纪了,到底走的是什么路子?薄先生其实代表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很复杂的一个新路子,不一定是原来那种文人式的,也包括了民间的各式各样的东西。他自己不仅写书,还讲学,这很重要,因为学问需要通过学校来传播,像现在美国的研究和教学是绝对一体的,所以美国所有的学者基本都是教书匠,薄先生很早就开始这个路子了,就是写作和教学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将来回顾美院美术史系的历史,包括中国的这一套美术史的教学和研究方法,薄先生代表的这条路是值得思考的。
王连起(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在座的都是薄先生的学生,都是大学生。我没上过大学,到现在的学历还是高中生,而且是“文革”期间的,我能坐在这里感到很荣幸。我虽然没有受教于薄先生,但看过薄先生的书,了解薄先生对美术史论的熟悉程度。最近我也接触了一些学生,包括一些学校的老师,回过头来发现美术史基本的知识太重要了。要说中国的艺术有多高深,其实很多就是熟,哪怕现在是专家教授了,基础没打好,也很容易让人看出破绽来。所以这一点我是非常佩服薄先生的,这么多参天大树都是您培育的,做老师实际上是很幸福的事。启先生说,揽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所以说教书匠,这个匠字有两种,工匠跟大匠、巨匠不一样的,薄先生的匠不是一般的匠。
朱青生(北京大学教授):
我突然发现我们是在集体做一个学术口述史的梳理和补充,特别有意思。我在美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听过薄先生的课,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薄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次启功先生来上宋代绘画的课,带了一批宋代册页,上完课后发现少了一幅,薄先生非常着急,结果启先生说没有关系,找到了再说,就回去了。过了很长时间,有一天薄先生看画册时无意间发现了这幅册页,原来是当时为了跟印刷品做对比就夹在书里面了。薄先生就立刻给启先生送回去了,启先生拿到后哈哈大笑,说我叫你不要着急吧。这个故事给我们影响很深,而且这种影响会通过我们的理解、我们的身体永远地流传下去。所以我说薄先生给我们的不仅是教育,而且是直至终生的影响。
后来我到德国留学,阴差阳错的以年画为选题做博士论文,但这方面内容我以前接触有限,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就专门回国来向薄先生请教。薄先生让我去武强体验制作年画,我当时除了没有刻板以外,整个印刷过程都做了,同时还调查了50年代武强年画的所有纪录,最后论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所以我博士论文的导师实际上有两位,一位是德国的雷德侯先生,一位是薄松年先生。我在写论文的时候接触到一位德国海德堡的医学教授,他对年画特别感兴趣,后来我把他介绍给了薄先生,他们二人就成了朋友,薄先生帮助他建立了一套门神的收藏,这批藏品现在好像交给了海德堡的人类学博物馆。
薄松年:刚才有一个事情你记错了,我当时不是这样讲的。启先生在美院讲书法,带来一些书法原迹,讲完课后说可以留下来给学生看。我当时很紧张,生怕会出问题。同学看完后,我就小心翼翼地点好数,把作品收起来送还给启先生。交给启先生的时候一个一个点数,点到最后发现少了一件东西,是一个小幅的唐人写经,我当时汗都冒出来了,心想这怎么办?启功先生一直说不用着急,不要紧。这要是平时一些人,不要说没有了,就是外人想看一看都不可能,更何况拿到课堂,课后还留在那给同学看。最后发现这幅唐人写经不知道怎么的跑到一个经折装的背面去了,送还给启先生时,他说,你着什么急?唐人写经是小事,把你急坏了是大事。我每次想起这件事都想哭,这是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件事情。
还有就是大家说到我经常参加研讨会,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每次参加研讨会我都有一句话:我是知识老化,观点陈旧,信息不灵,记忆力衰退,现在各方面发展都很快,我到研讨会是来学习的。即便是一个年轻同志的发言,我也是仔细听的。
孟嗣徽(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我不是央美的,我是中央工艺美院77级的学生,毕业以后到宁夏博物馆工作,参加了须弥山石窟考察,到故宫工作以后又在工艺美院上了研究生。在故宫工作的时候我的兴趣点转到宗教美术史上面,这方面薄先生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我的第一篇论文写的是炽盛光佛变相图的研究,当时在余辉的介绍下向薄先生请教,薄先生特别详细地指导我,所以说我的研究基础是薄先生打的,这是我的第一篇文章,虽然写的时间很长,但写完后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后来我的研究就顺着这个路子进行了。
最近,我在做杭穉英家族的艺术家族史研究,也查了一些民间美术方面的材料,我发现薄先生在1957、1958年写了《为擦笔年画说几句话》的文章,当时擦笔年画处在被压抑的地位,薄先生敢写这篇文章让人很佩服。
曹星原:《宋元绘画研究》这本书的题名是朱乃正老师生前题写的,我想复述一下朱乃正老师对薄先生的评价,他说,第一,薄先生在美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先生,无论学问做得多么严谨、多么有影响,永远是一位有平民精神的人。第二,有些学者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舒服,而薄先生是一位很少不舒服的人。薄先生第一是学问很高,第二是人品很高,第三是永远朴实、有平民精神,朱乃正老师认为平民精神是高级知识分子人格的一种体现。
尹吉男(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我原来在北大学习考古,1984年到美院学习。当时零星听过薄先生的课,印象里薄先生讲课很生动,很有激情,并且博闻强记。当时我有一个偏见,认为学考古的人记忆力特别好,因为考古记忆的内容没有逻辑性,记忆难度很大。但我发现薄先生和美院其他几位教绘画史的老师都可以大段地复述画论,这就颠覆了我原来的想法。
余辉:刚才收到林通雁(陕西美术出版社编审)发来的短信,他说:在过去的60年里,薄先生在中国美术史教学及教材编写、中国绘画史、版画史、民间美术著述方面成就卓著,影响深远。在母校读书以及从事教学出版,尤其是担任《中国美术史教程》责任编辑期间,先生教诲深刻,我受益良多,先生的做人和治学精神始终激励我勿忘学业,勤于笔耕,以学术成绩回报师长和母校,借此机会谨向先生表达我的深深敬意和谢意!
(文稿整理/栾林 摄影/李天垠、姜润青)

暂无评论